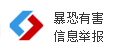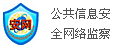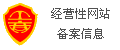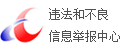|
“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”的诞生,与上世纪80年代解放思想、改革开放的环境氛围,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精神的唤起,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且不论那场源于上海,影响深远的“戏剧观大讨论”;单就那引人瞩目的上海市花遴选,似乎就是为呼之欲出的戏剧表演艺术奖造势,将“白玉兰”的响亮名称赋予了她。而“白玉兰奖”,确乎是以她35年的历程,兑现着人们寄予的上海市花白玉兰“争先报春,朵朵向上”的品性。
作为一个艺术奖项,“白玉兰奖”的评奖范畴定位于“戏剧表演艺术”,这是一种颇具前瞻性的独特构想。其独特性,就在于概念的宽泛性与内涵的聚焦性相结合。她将传统的戏剧概念进行了外延的拓展,延展至一切以舞台为支点的表演艺术,涵括了戏曲、话剧、歌剧、舞剧、芭蕾,直至音乐剧、杂技剧等,也是对行业界限的逾越和突破。然而,她又陡然地在如此宽泛的艺术形态中,将评判的目光聚焦于舞台的表演艺术,即演员之表演。这一独特性,在今天的中国艺术界仍属首创,尚无出其右者。
由此,“白玉兰奖”的价值和意义,首先在于她直截了当地触碰了所有舞台艺术的终端显现——演员之表演,凸显了舞台艺术创造力的核心问题。其次,将不同舞台艺术表演置于同一平台予以评判考量,在客观上推进不同艺术形态之间的交流、学习和相互启迪,有益于激发艺术创造力。
“白玉兰奖”的这种独特性,无疑对当代戏曲表演艺术具有显著的价值引导作用。
众所周知,戏曲素来倡导“以演员为中心”。尤其是京昆等程式化表演体系发育相对完备的剧种,对演员的程式表演的规范性有着严苛的要求,这本来是一种根源深厚的艺术优势。但是,这种优势倘若被引向极致,其价值评判又被局限于剧种或戏曲行业相对闭环的状态下,也容易使其在艺术表演在价值追求方面处于迷失的状态,进入到“以表演演员为中心”。其典型的表现,便是游离人物的程式技艺卖弄和对剧场效果的取悦。更有甚者,在观念上认为京剧表演就是卖“玩意儿”,而疏于人物刻画。而一旦将戏曲与其它舞台艺术置于同一个平台后,势必逾越戏曲自身评判的局限,开始接受更为广泛的审美评判,乃至严苛的市场和观众评判;进而为戏曲表演艺术提供了折射时代文化观念的参照坐标,有益于激励戏曲演员对表演艺术新境界的追求。印象中,第一届“白玉兰奖”主配演奖的获得者中,尚长荣、言兴朋、梁谷音、史济华等戏曲演员的占比颇大。从剧种或行业角度看,这些演员本身就是业界翘楚,但他们获奖的共同理由,是他们在新剧目中塑造了令人信服的舞台形象。
纵览“白玉兰奖”30多年的获奖名单,几乎揽尽了当今戏曲舞台上各个剧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,且不分南北,不论花雅。他们获奖的理由,固然也是基于他们所造人物形象的鲜活。同时,我们也能够看到,一些凭着“一招鲜”走天下的戏曲演员,尽管其名声不菲,不乏拥趸,却不入“白玉兰奖”的法眼。这,恰恰体现了“白玉兰奖”的价值倡导和作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30多年来“白玉兰奖”一直在致力于鼓励,乃至助攻戏曲表演艺术领域里的创造性劳动和创新性发展。
“白玉兰奖”的价值引导,并非滞留于观念层面,而是有着具体价值维度的。比如,首先是关注演员的基本功,进而是塑造力、表现力、整体感等,当然也包括艺德品行。这些考量维度,切中了舞台表演和创作机制中的若干关键环节,显现为颇高的专业评价尺度。同时,不失对不同舞台艺术样式本体审美特质的追求和评判,达成表演技术与表演艺术,抑或程式表演与人物塑造之间的平衡。如此,“白玉兰奖”在评判价值上,突破了小范围业内评判很容易出现的单一和偏颇,体现了符合表演艺术当代审美的价值追求。
作为戏曲表演从业者,倘若以为基本功是其职业追求的唯一,而忽视对艺术的塑造力、表现力、整体感的追求,则难有大的作为。当然,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,却也是困扰戏曲行业多年的问题。究其原因,恐怕是戏曲长期处于被保护被振兴的境遇有关,使得我们的戏曲界始终有一种剧种纵向发展中的失格忧患,由此催生了艺术观念和行为的固化现象。但戏曲艺术发展的历史事实,却一再提示我们,在坚持本剧种的审美精神下的创造性艺术贡献,才是防止剧种艺术失格的最佳作为。一如当年的周信芳、袁雪芬,而今的尚长荣、陈少云便是这样的艺术范式。这些艺术典范,实际上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精神具体而形象的持续彰显。“白玉兰奖”作为一个跨界的戏剧表演艺术评价的专业平台,对一代代青年戏曲人的影响作用亦是不能小觑。他们在各自的成长环境里不仅锤炼夯实着传统的艺术功底,更富有开阔的艺术视野和个性化的思辨能力。体现在表演艺术上,便是他们对戏曲表演更高境界的追求意识和努力。一批批年轻的戏曲才俊跻身于“白玉兰奖”,预示着戏曲艺术领域蕴藏着蓬勃的创造活力。
|
 茂栋在线
茂栋在线 茂栋在线
茂栋在线